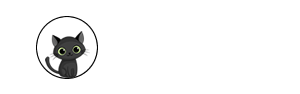美国老想让亚洲国家都怕中国,好体现自己的价值

近日,特朗普政府任命曾发表挺以色列言论的右翼网红亚当斯(Nick Adams)担任下一任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这一举动迅速在这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引发巨大争议。专注于东南亚问题的政治分析师威尔士(Bridget Welsh)则称美国这么干,可能“会把所有东南亚国家都推向中国怀抱”。
威尔士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美国政策专家埃文·费根鲍姆博士在播客频道“太平洋两极”(Pacific Polarity)对话时,就曾表示,由于美国在亚洲的政策不顾域内国家的需求,偏重于针对中国的安全考量,美国的影响力将在十年内逐渐从区域淡出。
埃文·费根鲍姆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总裁。他此前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多项高级职务,包括南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中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专注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离开政界后,他深耕智库领域。
演讲内容由观察者网整理并发布,供各位读者参考。
【翻译/ 李泽西】
理查德·格雷:在本期《Pacific Polarity》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埃文·A·费根鲍姆博士(Dr. Evan A. Feigenbaum),您的博士研究方向是中国政治。此后,您的职业生涯扩展到了东亚、南亚和中亚,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承担了相关职务。当下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背景下,是什么促使您将目光放得更广,看向整个亚洲——一个涵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区域?在您看来,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是否存在一条连贯的主线?
埃文·费根鲍姆:我最初的职业生涯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通”路线。我拿的是中国政治博士学位,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还当过专注中国话题的老师。然后,我加入了政府,在此期间,我开始担任涉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职务。
我有时会开玩笑说,我的职业轨迹与成吉思汗不谋而合——从亚洲的一个地区“横扫”到另一个地区——当然,我没有沿路征服任何地方,但确实得以涉足多个区域。
这其中最有趣的是时间点。就像你说的,这一切都发生在2000年代的头十年。那是亚洲各个次区域重新实现经济、金融乃至一定程度战略整合的时期,这种整合在很多方面更接近亚洲历史上的自然格局,而不是我有时称之为“冷战异象”的结构。
以中亚为例。作为苏联和俄罗斯帝国组成部分期间,亚洲原有的自然连接——通过贸易路线、宗教传播、思想交流等——很多都消失了。印度和东亚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用的许多地名都能看到印度在东亚的历史遗产,比如“印尼”、“印度支那(Indochina)”,柬埔寨仍保有印度教寺庙,这些都是历史的痕迹。但在英国殖民体系下,印度与地区更广泛、更自然的联系被人为割裂。

埃文·费根鲍姆(资料图)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
所以,正当我个人和职业轨迹从单一聚焦中国转向更广阔的亚洲角色和责任之时,这个地区本身也正在经历一场不仅是转型,更是一种“历史上的回归”。
例如,在中亚,中国现在是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和投资伙伴。虽然今天的背景与历史不同,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中国在中亚“前俄罗斯时期”扮演的历史角色。如今有大量亚洲资本在亚洲内部流动,寻找投资回报,这是我二十几年前刚入行时根本看不到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亚洲正在回归一些历史上的模式与常态——这些模式更自然,也定义了亚洲区域的演变,只是在后来被一些人为的政治、战略与体制结构打断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美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这样一个“更加亚洲、而非太平洋,更加一体化”的地区?如果你了解我的研究,你就会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回答是否定的:不,美国远未准备好。
因此,我认为,20年后的亚洲将与我1990年代刚进入这一领域时看到的样子大不相同。
理查德·格雷:2009年,您和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联合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撰写了一份特别报告,题为《新亚洲中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w Asia)。回头来看这份报告,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如今美国的做法几乎正好与你们当年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或者说只有少部分建议被采纳,而且效果甚微、且基本消失了。你们当时强调了参与多边对话的重要性,而历届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在持续参与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太清楚美国在与东盟这一机构合作方面到底有怎样的愿景,而距离最初建立这种合作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即便拜登政府采用了某种“格子结构”式的联盟制度构建方式(latticework approach),其中也并非所有框架都包含美国,其内容又极度偏重安全领域,忽略了一些关键的经济要素;而即便是这些安全支柱本身,其未来走向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些安全、经济、制度性元素之间的问题非常复杂——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引用您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是否真的成了亚洲的“黑森佣兵”(Hessians)?
埃文·费根鲍姆:首先,我觉得有必要稍微回溯一步,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美国在这个世界地区成为了领导者?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前投射十年,支撑美国领导地位的那些支柱,是否还会和十五、二十年前,甚至是冷战背景下的那些支柱一样?
我在2012年与罗伯特·曼宁联合撰写的另一篇文章《两个亚洲的故事》(A Tale of Two Asias)中提到过,美国之所以在亚洲长期扮演领导角色,不只是因为它是安全保障者,更因为它为该地区提供了大量与经济相关的公共产品和其他利益。
在安全领域,美国基本上维持了和平。无论是其盟友,还是那些虽非盟友却从美国提供的安全中搭便车的国家(通过同盟机制、海外驻军、航母战斗群的存在等),这种安全角色提供了某种“安全毯”,使得除中国和朝鲜之外的所有国家,都能在这一保障下追求自身目标,包括发展、增长与繁荣。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支柱。美国之所以是该地区的领导者,不只是因为它是安全提供者,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导者。正是美国市场的需求支撑了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路径。而美国也一直是规则的制定者、标准的制定者、规范的推动者。
这就是传统角色。时至今日,我们就必须退一步问:美国如今的政策和姿态是否仍在扮演着既有的安全角色,同时也扮演着那个经济角色?在第一个问题上——安全领域——我的回答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的。因为多数国家都惧怕中国,仍希望美国存在于该地区。
但在经济领域,如果你往前看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美国领导力的经济支柱很可能会在相对程度上减弱,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美国仍将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与本地区所有国家的贸易额在绝对值上都在增长,但在相对值上——即在各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却在普遍下降。看看中国二十五年前和今天在亚洲的地位差别就明白了。
此外,在多届政府,尤其是本届政府的领导下,美国越来越被认为是在关闭自身市场、提高壁垒、不愿参与那些设定规则或制定标准的协议。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美国力量配置。而这意味着,亚洲国家本身将越来越倾向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规则。

2017年1月23日,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路透社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局势与冷战或冷战后初期的格局已经截然不同。其次,还有一个问题——这正是罗伯特和我当年在那份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报告中所提出的:美国是否在适应这种变化?换句话说,如果亚洲国家开始联合制定规则,美国是否愿意、也是否有必要加入其中?如果出现仅限亚洲国家参与的机构、协定、共识,美国将扮演什么角色?例如,美国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外;美国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之外;美国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之外。
这就出现了一个趋势:亚洲规则的制定过程正在发生,而美国不是隔着玻璃往内看,就是干脆主动退出。这就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美国到底想怎样定位自己?
我最后想说的是:这意味着,美国正在面临一场信心危机——特别是在东南亚——关于它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愿意发挥什么作用、最终将发挥什么作用,以及亚洲国家该如何据此调整自身定位。
这不是美国在该地区第一次面临信心危机。比如1975年越战失败时,很多人也在质疑美国是否还能在该地区维持存在感。但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刻尤其重要,因为特朗普政府当前在一系列亚洲国家高度关注的议题上——企业、市场、人口、贸易、关税、保护主义、贸易条件等——所持的立场引发了广泛担忧,大家不知道美国究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我会说,美国并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个变化。这正是罗伯特和我在那份报告中所强调的:美国需要为一个更“亚洲化”的时代做好准备,不能再理所当然地假设自身处于中心地位。而我认为,在华盛顿内部,这种自我中心的假设仍然过于根深蒂固——大家认为,只要亚洲国家都怕中国,美国就可以永远是该地区的“天和地”(alpha and omega)。很抱歉,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
“要搞对中国政策,你必须先搞对亚洲政策”,美国已经把这个观点完全颠倒了
李泽西:最近在洛伊研究所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首席执行官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指出,由于高层的混乱,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在本届政府中拥有了不同寻常的权力。哈姆雷还形容科尔比是“一个思维异常单一专注与中国开战的人”。
与此同时,他的上司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演讲也同样聚焦于与中国的竞争,并称在座的其他人都是这项事业的“盟友和伙伴”。就像你所说的,这几乎让人感觉美国的整个亚洲政策都已经被简化为中国政策。这种趋势显然也超越了现任特朗普政府,是一种更长期的现象。
但同时,中国的确越来越强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无疑也放大了华盛顿内部那些主张采取这种“聚焦中国”策略的声音。那么,这种趋势是否还能改变?甚至说,这种趋势应不应该改变?
埃文·费根鲍姆:如果美国想要在亚洲地区保持相关性,它就必须回应亚洲国家本身的目标与诉求。现实是,第一,多数亚洲国家并不愿意与中国“脱钩”;第二,他们其实也没有“脱钩”的奢侈余地,因为他们的核心关切是:增长、就业、可持续发展、技能提升。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在本地区提供的机遇,几乎没有哪个亚洲国家是准备彻底拒绝的。
如果美国一味在整个地区到处宣传“把中国从亚洲故事中剔除”、“别要中国的钱”、“别用中国的技术”,它是很难获得支持的。大家都在说,美国需要一个有竞争力的提议,但问题不只是“竞争”而已,而是美国必须在竞争的同时,与亚洲伙伴共同设定竞争的框架和背景,从而影响中国在本地区的互动方式与姿态。
我在国务院时的一位上司,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最近刚刚去世。他是我在任职时的副国务卿,是资深的日本问题专家和亚洲事务专家。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要搞对中国政策,你必须先搞对亚洲政策”。我认为他的意思是,美国不可能总是直接左右中国的选择,但如果能与伙伴们一起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那么至少可以影响中国在制定自身政策路径时所面临的激励与制约。
而你刚才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指出,美国已经把阿米蒂奇的观点彻底颠倒了过来——本应“通过搞好亚洲政策以搞对中国政策”,现在却变成了“所有亚洲政策都从中国政策中派生出来”。而且这种趋势已经贯穿了几届两党的政府。
但问题在于,这种“中国中心主义”并不是大多数亚洲国家所认同的视角。
其次,美国对这种竞争的处理方式是完全安全化的。一切都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技术,是国家安全;人文交流,是国家安全;经济流动,是国家安全;中国投资,是国家安全。美国人是这么看的,但这不一定是马来西亚人的看法,甚至不一定是越南人的看法——即便越南对中国始终抱有矛盾心理。这种态度在该地区很难赢得共鸣;更糟糕的是,它削弱了美国本应向地区提出的有吸引力的方案。
那么,这种趋势是否还能被重新调整?你刚才问到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我认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治和两党共识性的轨迹,这种轨迹已经融入了美国的政治体系——也就是你说的那种“聚焦中国的安全竞争”,并试图将美国对整个地区的战略强行套进这种框架里。
而这正是为什么美国在四边安全对话(Quad)成员国外的国家里,很难获得它所需要、也本应拥有的影响力。在该地区,Quad的叙事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叙事之间存在巨大脱节。或许菲律宾是个例外,但你也知道,菲律宾每六年几乎就像换了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不能假定现在菲律宾的政策轨迹五年后还能持续——这就是挑战所在。
不具体评论现任政府的政策内容,我想说的是,当有一位像特朗普总统这样,既没有原则导向,也不具备战略视野的领导人时,很难想象美国会真正去构建一个目标是“塑造地区格局”的联盟,而不是一个狭隘、安全化严重、自我中心的联盟。
而这正是所谓“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的问题所在——如果你换位思考,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立场看,他们会问:“美国优先”是否意味着“我们垫底”?这个地区充满了实力可观、能力强、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中等强国,他们希望对本地区的未来拥有话语权。
而我只是认为,美国目前的政治轨迹并不适合去适应这一现实。也正因如此,我过去15年里一直不厌其烦地撰文说,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正在逐渐衰退。
理查德刚才提到我在另一个播客节目里说过的一句话,说美国正在变成亚洲的“黑森佣兵”(Hessians)——我们在这里航行舰艇、飞行战机,但在其他方面却严重缺位。可以设想,十年后,空喊‘中国威胁’将仿佛在嘈杂的剧院里一样恐怕难获共鸣。

黑森佣兵,是指18世纪受大英帝国雇用的德意志籍佣兵组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约有30,000人在北美十三州服役,其中近半数来自德意志的黑森地区。黑森佣兵是以小队为单位受雇,非单人个别受雇。文字来源:维基百科
尽管美国在域内多国眼中仍存在威慑中国的作用,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亚洲正迈入‘去美国化’的后美国时代。这就是我说的‘信任危机’:人们无法确信,除安全领域外,美国会以契合其目标的方式长期在场。
赫格塞斯对此并没有给出真正的回应,部分原因是他是国防部长,天职就是谈安全。但如果地区国家担心的是美国过于侧重安全,而在其他方面严重不足,那么你就不能把安全问题与更广泛的美国政策和战略态势切割开来。
如果美国在贸易上对大家征收各种关税,以至于妨碍了他们的增长与发展,就不能转头来说:“哦,我们是你们首选的安全伙伴,其他一切都暂时忘了吧。”在亚洲国家看来,这一切是有机的整体。
所以,我最后还是要回到我的起点:我认为,十年后的美国在亚洲的角色,会与历史上的角色大不相同。